林惠民:迟到了13年的大学梦
作者:林惠民,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
出处:《中国科学报》,2018年12月21日
我们这代人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这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感受到的。
命运的沉浮无法复制,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从小培养对知识、对科学的热爱。人生的选择很多,兴趣是第一位的。尽管科研这条道路充满坎坷,走得艰难,却也因此更有意义。追求科学真理、探索客观规律给我带来的快乐,是不可替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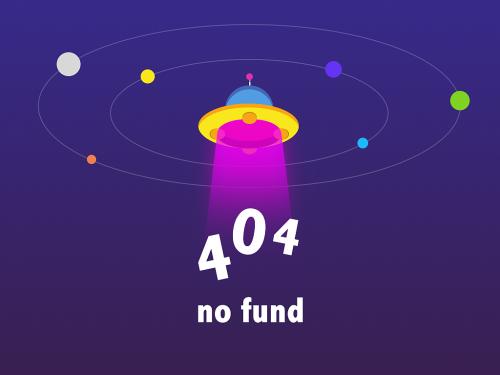
林惠民正在工作
我的求学生涯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帮助和指引,有的甚至影响我一生。如今,当我也承担起老师的角色时,我希望我能真正激发起学生对科学的热爱。
摘不掉的“只专不红”
我1947年11月生于福建福州。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福州市的普通职工,我是家里的独子。父母一直很重视我的教育,可我却天性顽皮。尽管也热爱学习,成绩拔尖,但并不把读书太当回事。
而且,在我的印象里,我也从未因为成绩突出受到过什么表扬。因为,我从学生时代就被贴上了“只专不红”的标签。解放前夕,我的亲戚中有人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于是,我就成了社会关系复杂的孩子。
1960年,我从我们那的名校——鼓楼第一中心小学毕业。尽管我的成绩很好,却只能进到当时城乡接合部的十八中读初中,学校环境、学习氛围和之前的差距很大。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印象最深的就是整天肚子饿。
当时我也没什么心思读书,特别调皮,初一时迷上了装矿石收音机,经常旷课上街买零部件。直到初三,遇到了教数学的班主任葛霖华老师。
葛老师是福州三中1958届高中毕业生,成绩优秀,但因为家庭成分原因,没能考上大学。我上初三那年,福州市首次举行初中数学竞赛。在葛老师的指导下,我参加了这次竞赛。
对待考试,我向来比较随意。因为粗心,有道相对容易的计算题被我算错了。一出考场,葛老师就迎上来对答案,知道我有一步算错了,比我还着急。不过最终,我还是拿到了二等奖。这在当时的十八中,是件了不起的事。
中考前夕,葛老师把我推荐给福建省数学名师、时任福州三中数学教研组组长的池伯鼎老师。高中还没开学,我就和三中其他两个同学一起,在池老师指导下超前学习数学。所谓“超前”,就是在高一学完高中三年的数学课程。
比我高一级的学长吴忠超,是池老师培养的第一位超前生,提前二年参加高考,被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这也是池老师对我们的期望。
开学后,我们每周六下午或晚上都到池老师家,学习高中的数学课程。高一下学期(1964年),我们参加福州市高中数学竞赛,与高三的学长同台竞争,我再次拿到了二等奖。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1964年夏天高考招生时,池老师曾把我推荐给中国科技大学在福建的招生组,对方已经同意破格录取。可最终因为不“红”,我的大学梦迟到了13年。
而立之年的考生
1966年,“文革”开始,6月中旬广播里传来了高考推迟半年的消息,不久高考被正式废除。
1969年,我来到闽北山区建宁县插队,和农民一起种田挣工分,体验到了农村生产方式的落后和农民生活的艰辛。
1972年12月,因为照顾独生子女政策,我得以回到父母的身边,成了福州最大的重工业工厂——八一磷肥厂的一名工人。由于户口问题没得到解决,我们新招入的几十名前知青只能在各个车间打杂,大多是三班倒的重体力活。
户口“解冻”后,我比较幸运地被正式分配到了机修车间,当铣工,负责加工各种齿轮以及在工件上开槽。这时我的几何和三角知识派上了用场。
1975年,我们厂开办 “七二一”工人大学。厂里知道我数学底子好,让我教数学。
此前我曾利用业余时间在福州大学旁听过日语课,于是便到福建省图书馆外文部借了一本日本专科学校用的微积分教材,翻译成中文当课本。
1977年秋天,传来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开始我以为这是针对在校生的,没有在意。后来的消息说“老三届”学生也可以参加高考,这让我喜出望外——想不到离开中学11年了,我还能有机会考大学。
不久,《福建日报》公布了在福建招生的大学及专业。因为需要在家照顾父母,我首选了福州大学(以下简称福大)数学系。数学系只招两个专业,基础数学和计算数学,各30人。计算数学注明是“机密专业”。我报了基础数学。
机会是来了,但要求很苛刻。福建省高招办规定,超龄学生必须有“专长”才能报考。我带上了两次数学竞赛二等奖的奖状,还有翻译的日文教材,来到工厂所在地的报名点——新店小学报名。没想到招生办的工作人员认为这些材料不能作为有“数学专长”的证明。我的大学梦险些再次落空。
池老师知道了这个情况,叫我到他家里。那时他得到平反还不久,居室窄小。他特地为我写了一封长长的推荐信;为了表示郑重,又从抽屉里找出一颗最大的印章,端端正正地盖在落款处。第二天,我拿着池老师的推荐信,再次来到新店小学。报名点的工作人员是新店小学的老师,他们都知道池老师的大名,看了他的推荐信,立即就让我报了名。
那时我住在市中心一座老式住宅的花厅,比较宽敞,同学、朋友们常来我家聚会聊天。高考前夕,我家的饭厅成了老同学们复习备考的课堂,我们戏称“互助组”。这些年已三十、饱经风霜的“而立”辈,围坐在饭桌旁,重新开始啃课本、做习题,互相帮助、释疑解惑,实在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我的考场在福州市第十九中。那年的试题对我显得简单,尤其是数学,我驾轻就熟,做得飞快。我有自己的做题习惯,喜欢做难的,对容易的提不起劲。对难度大的题,我还喜欢多想几种解法,即使考试也如此。那年高考数学试卷有一道20分的附加题,我写了三种解法。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也是事后才知晓。
当时,十九中考场的监考官发现我用了不到一半的时间就做完了数学试卷,怀疑出现泄题,便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时任省高招办数学科评委会主任的池老师。池老师立即赶到现场,从窗户外看到“出问题”的是我,立即打消了监考官的疑虑。他说,“这是我的学生,他早就可以当这些考生的老师了”。
我没有辜负池老师的期望,高考得到了358分外加数学附加题20分的高分。
晚来的人生春天
这次高考成了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1978年春节前,我收到了福大数学系的录取通知书,我和父母都特别高兴。更幸运的是,我在工厂已有5年工龄,按当时的政策,可以带薪(每月37.5元)上大学。父母当时都已经退休,这为他们免除了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唯有一点令人不解的是,我被录取的专业是“软件”,而不是报名时的“应用数学”。事实上,高考报名时,《福建日报》发布的福大招生目录中并没有软件专业。“软件”是什么?我一无所知。问老师亲戚朋友,也没人知道。
春节后到福大数学系报到,我迫不及待地问接待报到的老师,得到的回答是:软件专业是给计算机编程序。我心里不禁有些疑惑。当时涉及计算机的专业都属“机密”,我有海外关系,将来会不会出问题?不过这点疑虑很快就被“终于上大学了”的兴奋感驱散了。
当时我们软件班招了30个学生,我是唯一的“老三届”,30岁,班里年龄最小的才15岁,我一个顶两个。但我并没有“老”的感觉。“文革”十年,我们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如今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心里充满了阳光。

林惠民为北京市公务员作科普讲座
经历了插队务农、进厂当工人,感受到我们国家贫穷落后的状况,对于学习,除了个人爱好,又多了一层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当时有一句流行的口号:“把被四人帮夺去的时间夺回来!”入学后我把几乎所有的业余喜好都抛开了,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学习上。
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学习和生活条件还相当艰苦。学校教室不够,我们一、二年级的很多课都是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教室上的,地面是略微夯实的黄泥土,一到雨天就满地泥泞,条件十分简陋。但我们像久旱逢雨的禾苗,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营养,忘记了夏天的暑热和冬日的寒冷。晚上,老师们不顾白天讲课的疲劳,主动到教室和宿舍为同学们解答疑难。这些感人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系里为我们配备了最强的师资。一、二年级我们和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的同学一起上基础课。教我们数学分析的魏祖烈老师早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比陈景润高一届,上课不看讲义,边讲边在黑板上写板书,概念清晰、推理严密、环环相扣,让我们沉浸在数学和逻辑的内在美中。
我中学学的是俄语,后来在工厂期间自学了日语,从没碰过英语。入学后的英语摸底考试我交了白卷。大学一、二年级我在英语上花了不少时间。两年后我的英语考试成绩升至全班第一。
现在看来,福大数学系77级开设软件专业,是一个非常大胆、前瞻的决策。当时软件方面的很多专业课程还缺乏师资,我们开学后系里才派出教师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等处进修。大三开始上专业课,外出进修的老师还没有全部回来。我们专业课程开得不多,每周只上十六七学时的课。到大四更少,每周就十三四学时。这给我留下了大量的自学时间。我大部分课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埋头钻研,查阅专业期刊资料。
软件专业的一门主干课是编译原理,任课的何天牧老师多年来跟随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九室(软件所的前身)的唐稚松先生从事程序设计语言和编译技术研究,选用的是原版英文教材。大四又开设了关于唐先生设计的xyz语言的讨论班,使我们在本科阶段就接触到了研究的前沿。毕业前夕我将关于程序语言中类型问题的学习心得整理成一篇论文,发表在《福州大学学报》上。那时学到的程序语言与编译系统的知识,在我日后做博士论文以及在英国从事并发验证工具研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大学计算机系课程开设多而杂,学生每天忙于上课、应付作业,几乎没有自己思考问题的时间,缺乏主动思维的训练。这样的培养方式,不能适应科学创新的需要,令人担忧。
大学4年,我的所有考试科目成绩全优。毕业分配被系里留下当助教。两年后,我以同等学力考取科学院计算所九室唐稚松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迈进了从小向往的科学殿堂。
在福大的4年大学生活,为我后来的进一步学习和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留下了我人生中一段最美好的记忆。

诵读人:软件所 殷效菡 业务主管